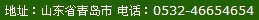|
乌鲁木齐最好的白癜风医院 http://m.39.net/pf/a_4484869.html 今天中午,国家电影局终于发布了7月20日低风险地区影院可以开门营业的公告,全国百万电影工作者,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。 影院歇业的这半年间,电影制作、发行、院线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了毁灭性打击,影院倒闭、人才流失、股票狂跌都是直观的产业效应。没有新片,没有话题,产业链的崩断甚至影响到我们所认为「因疫情获利」的流媒体,而现实的状况是因为缺乏话题流量和硬质内容更新,它们的日子也没好过到哪里去。 除了实业家们资产缩水、营销者们家中断粮,作为我们的观众也同样焦头烂额。少了院线新片,每周的娱乐生活就仿佛少了一大半。虽然我们也感叹电影在历史上能够跨越技术、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反复跌宕,能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开门迎宾,但最终没能挺过新冠疫情(这也是好莱坞年历史上第一次停业)。 疫情期间,观众在心里渴望着一切娱乐形式,这种情结即使不能称为「迷影」(cinephilia),却也必然指向迷影者的庙堂——电影院。在多年的历史上,正是电影院这一建筑形式,保存了电影艺术完备性的火种,让它没有沦为一种泛媒体化时代的博物馆艺术。 至少,在疫情之前我们的院线和银幕数量仍在增长,年国内新增银幕块,年又新增块,这种增长预示着去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。即使我们如今有了各种便利的观影工具以及诸类便捷的观影渠道,但就如苏珊·桑塔格在「百年电影回眸」(TheDecayofCinema)中所哀叹的那样:「两种屏幕的尺寸差异巨大,影院中远远大于真人的实景画面不同于家里电视匣子的小画面。」 即使你在家里将投影放大到整面墙的尺寸,它与电影院的效果仍具差别,比如投影光的强度和银幕材质。即使你在自己的家中安装了西奥·卡罗米拉基斯(TheoKalomirakis)设计的顶级家庭影院,整体的感受仍然不能同影院相比,因为它有违观影活动的初衷——去电影院,然后和陌生人在黑暗中坐在一起。 看电影的归属感来自于集体观看一部电影的状态,以及不同地方同时放映一部影片的事实。人们通过影院与之遭遇,让影院成为一种感情扭结或者迷影活动的温床。去影院看电影不止是一种产业活动,也是一种社会需求,它提醒我们正在认真对待电影这种商品/艺术,也暗示着电影本身是一种「民主的艺术」: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,都可以混杂地坐在一起,享受同一部电影。 在历史上,这一需求促进了影院的标准化,推进了公共场所的道德化(陌生男女可以在影厅中近距离挨坐),更缔造了一个时代——罗克西·罗萨菲尔(RoxyRothafel)所创建的豪华影院联盟,也就是我们所称的「巨型影院」或者「电影宫」,其中甚至包括在天花板上绘制大片天空或者在侧墙上描绘风景的「气氛影院」(atmospherictheaters)。 -年代的影院建筑堪比宏伟的大教堂,甚至是很多电影在教堂中被放映,对此朱塞佩·多纳托雷的《天堂电影院》中均有揭示,然而就像这部影片中影院毁于大火又在原址上重建一样,影院这一建筑模式也经历了巨型影院的陨落、汽车影院的热潮、年代的生存危机(与电视竞争),以及今天复兴的多厅影院甚至以此基础打造的电影娱乐城,这都证明了影院作为一个基地/堡垒,让电影在电视、录像带、DVD以及今天新媒体产品的轮番冲击下平稳度过了一百二十多年。 我们不妨回到巴赞名作《电影是什么?》的那个问号,电影常常被理论研究者视为某种技术综合体,也就是放映机-胶片-影院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系统。然而,今天的放映机已经被数码投影所取代,胶片也已经转化为影片数据和密钥,那么电影院就成了电影最后的庇护所——只要对电影院观影的投射-认同效应不减,电影就会继续存在。 我们在此看到了技术之更迭和电影院之永恒背后的逻辑:电影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,而非一种技术体系存在。这也是安德烈·戈德罗和汤姆·冈宁等人在谈论电影诞生于何时的最重要论据,在他们看来,电影诞生于年前后,不但是因为电影语法在那个时候确立,也是因为我们告别了街头杂耍放映(罗西克的集团化放映经营大致在这一时期),电影院这一标准建筑形式成为电影业不可分割的部分。 时至今日,我们经历了数码取代胶片的过程,影院却仍然是电影产业的终点,也是发行的末端。 即使是雄心勃勃想要开凿一条平行发行链条的奈飞公司,也曾幻想让《爱尔兰人》等影片在多个院线上映,这受到了院线托拉斯集团的抵抗,这一抵抗正如国内电影从业者对徐峥的抵抗——当徐峥将电影发行卖给「字节跳动」的那一刻,我们就知道这属于电影「被浪费」的过程,《囧妈》在电视、平板和手机上呈现的效果必然与影院天壤之别,影片所引发的热度和讨论也远非影院上映时可比。对此我们深有感受,但我们也知道,新媒体网络求生的这一步必然要走出去。 然而我们也同样期待「网络大电影」到电影院的这一步能够走出去,就像奈飞的精品制作最终能覆盖院线。马丁·斯科塞斯曾经一度对观众的观影效果表达了他既往的担忧,屡屡告诉观众「不要用手机来观看《爱尔兰人》,至少也得拿个iPad来看。」如果这种「重返故园」能最终实现,我们就不必担心电影因「网络出走」而引发的巨大分裂,而网络发行仍然是电影发行的后续或者构成部分。 电影固然可以扩展到影院之外,扩展到居家场所、电视、iPad和手机。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影院的存在,具体来说,这是一种特定愉悦的需求,也就是一种仪式和气氛,说的更抽象些,是我们拒绝改变一种电影的「原初经验」,无论这种经验是富足还是贫乏,抑或我们只是部分地执行它——不是在电影院里全神贯注,而是伴随着拍照打卡、中途打电话、
|
当前位置: 胶片 >电影院,四天后见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
时间:2022/12/30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一位喜爱玩弹珠人的小学生,在老师指导下写
- 下一篇文章: 别犹豫了,下回拍照就用傻瓜机